最近到处都在铺天盖地说预制菜要进校园。
要搁以前,我是不太爱操这些闲心的,但眼下境况不同了。我女儿明年就要上小学,虽然学校很近,就在我家楼下,下楼出小区门左转200米就到,但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早已不允许父母们中午回家开火煮饭,一家人整整齐齐吃完饭再美美睡上一场午觉,下午再各自去上班上学。所以不管离家多近,中午这顿饭,无论如何都是要在学校里解决的。
对预制菜进校园的批评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上。我倒觉得这个攻击点选的不太好,甚至有些糟糕。在严格监管,规范制作的前提下,预制菜大概率比传统的后厨模式干净、卫生、安全的多。但这是有限定条件的——“严格监管,规范制作”——政府早已陷入“塔西佗陷阱”,哪怕上面政策是好的,人们也不再相信下面执行的人同样能执行好。更何况,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个什么预制菜进校园,摆明了就是来割老百姓韭菜的,老百姓自然更加不信这事儿能搞好了——边割老百姓韭菜还边让老百姓念你们好,可能吗?
另一种批评的声音,倒是更贴近预制菜进校园的痛点究竟何在。批评者居心叵测地恶意发问:“为什么公务员们两三块一顿饭就能吃上现炒现做的伙食,学生们一顿饭连自费带财政补贴一十二块钱,却只能吃预制菜?”

吃饭,从来不仅仅是“吃饭”。哪怕在人类先祖茹毛饮血的时代,“吃饭”也带有强烈的社会学含义,首领自然要先吃,其次是身强力壮的男性,再次妇孺,最后老弱病残。后来物质稍微丰富了一些,还要组织大规模的“祭祀”,大量的牲口、珠宝、甚至活人,献祭给神灵,让神灵“吃饱吃好”了,给族群开个后门,继续保佑。
“吃什么,怎么吃”,从来就是个阶级问题,社会问题,权力问题,而非一个单纯的温饱问题,营养问题,健康问题。
电影《雪国列车》中,最末等车厢的人们只配吃由蟑螂肉打碎再用果胶黏成的“蛋白质块”,就这还要实行配给制,定量供应。最末等车厢的人最初只是想填饱肚子,当他们发起革命,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向前冲杀的时候——在电影的设定中,车厢被设定为阶层(其实在电影语境下,我更倾向于阶级这个词)划分——发现越往前,食物的差别越离谱,最开始是能吃上鸡蛋,后来是新鲜的水果,再后来是上等的牛羊肉。最后的场景是,在优雅的西洋乐调中,一群满身血污,衣衫破烂的半野蛮人,坐在散发着幽蓝光芒的巨型水族箱前,品尝着新鲜的鱼刺身。
他们本来只是想多要几块蟑螂肉制成的蛋白质块,现在,他们要彻底摧毁这趟列车——哪怕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
每当说起预制菜,我脑海里便第一时间浮现出《雪国列车》中这个场景:无数只蟑螂,无数只触角和爪子还在疯狂扭动的蟑螂,无数只经历了无数次轮回——在污秽中新生,又在污秽中死亡的蟑螂,被投进一口散发着诡异光芒的张着血盆大口的机器。镜头一转,最末等车厢的人们正温顺地排着队,从传输带上依次拿起属于自己的两块蛋白质块,面无表情地塞进嘴里。

《雪国列车》剧照
有段时间,我还挺喜欢去吃个猪肚鸡,喝个菌汤什么的,每次还都要多喝几碗汤,那时我还认为那玩意儿能“养生”。后来知道了,都他妈是预制菜,科技与狠活,全是半锅清水,半锅不明成分的白色粉末兑出来的,我便一口也没有再吃过。不仅没有再吃,仅仅是想一下每一口咽下去,就有半口不明成分的白色粉末,我就血压飙升发,仿佛那不明成分的白色粉末已经在我血液中扩散,并击穿了血脑屏障,令我头晕目眩。
让我把话说得再直白一点。尽管看起来温情脉脉许多,预制菜的味道可能很可口,预制菜的包装可能很精美,预制菜的卫生标准甚至可能会更严格,但它在本质上,与《雪国列车》中的蛋白质块没有区别,与我们每天例行公事给宠物猫宠物狗饭盆里添上的猫粮狗粮没有区别。
预制菜的危害从不在于它能不能吃好不好吃健不健康,而在于你一旦吃了预制菜,就相当于接受了这样一种设定,自愿地把自己置于宠物猫宠物狗的地位,自愿地从小打上这样一种思想钢印,有些人天生该吃深海鱼刺身,有些人天生该吃蛋白质块。
想想现在的小孩儿就觉得很可怜,从上幼儿园开始,部分更早的,从幼托开始,就开始吃大食堂,一路从小学吃到初高中,吃到大学,哪怕毕业工作了,成家立业了,一年到头也吃不了几顿正经八百烹饪的饭,不是学校大食堂,就是街边小餐馆,一辈子百分之八十的饭都献给了预制菜。整个吃蛋白质块的一生。
我旗帜鲜明地反对预制菜进校园,尽管我们早晚都要吃蛋白质块,但我还是想让那一天迟一点降临到我女儿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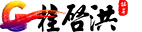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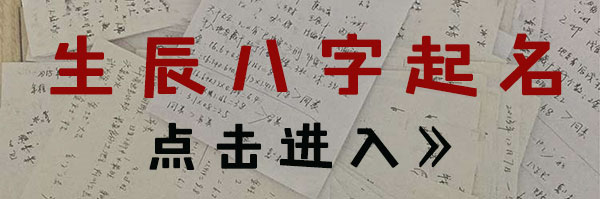















最新评论
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
现在是短视频的时代,认真做个人博客的很少见了,真是难能可贵。
拼多多砍几刀太烦了,一直让砍
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
不要把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地震能把铁路都震弯
知道了
这样的问题居然还需要分析?但凡脑子正常点也知道公司无责